上個禮拜六(5/2)和板橋社大、媒觀志工一起去三鶯部落的時候,紀錄片導演馬躍比吼和人民火大聯盟的柯逸民都提到部落拆遷的背後涉及的開發利益,以及政府或都會中產階級對河濱地利用的想像。
剛好最近讀到一篇1991年的文章(〈空間分離主義與法律根源〉,1991,《當代雜誌》第六十三期)在談台灣都市計畫的問題,雖然距離現在已經將近二十年了,但許多觀點仍然非常進步。比如文章裡提到:空間上的分離主義正是一種促使建築與都市分離的想法和作法。換言之,在這種作法下,建築不再是一個構成實體社會的成員,而只是佔據一定空間的有產權的物體,它與都市不發生關係,這時,都市將不再是一個空間的社會,只是一堆物質材料的集合。但是,建築與都市的分離而造成都市的瓦解,卻是合法的產物(王槐三,1991:120)。
這讓我想到近年來非常時尚的都會水岸生活的風潮,住在水岸景觀住宅旁,下班可以到附近的河濱公園散步,假日還可以沿著腳踏車道一邊運動一邊遊玩。這樣的生活型態本身並沒有錯,但是如果建築與都市計畫是一種讓人、社會與環境能夠和諧共存的專業技術的話,為什麼這樣的生活型態容不下河岸部落的存在?有多大的技術困難嗎?還是其實原因不在工程技術,說穿了也只是著眼於自身的目標與利益,因此任何有可能阻擋目的達成的因素都必須除之而後快?單以違法、違建的名義驅趕都市原住民是具有正當性的嗎?
在都市發展的歷史裡,原住民往往是被驅趕的族群,那天自救會成員潘金花談到小時候台東池上老家的土地被逐步侵吞的經驗;座談會上自救會發言人洪鳳琴也提到海山煤礦事件的歷史,礦坑爆炸造成許多阿美族礦工喪生,生還的族人最後選擇三鶯橋下定居。
三鶯部落的形成是許多社會、歷史與文化條件相互作用的結果,如果沒看到都市原住民的生存狀態、被漢人驅趕的歷史,以及「逐耕地而居」的文化,就沒辦法理解他們為何堅持就地居住。
同樣的,在都市計畫或公共建設的決策過程中,如果刻意忽略河岸部落形成的社會、歷史與文化因素,將造河岸部落居民和其他都市成員的對立。在三鶯橋下的三鶯部落,算不算自然形成的都市的一部份?這個聚落對附近的環境造成什麼影響或改變?在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引發社會討論的時候,政府的技術官僚就急著一次又一次地把部落剷平,雖然理由是為了整建美麗的都會河岸,好讓都市居民有更舒適的遊憩空間,實際上卻將都市居民與河岸部落居民區隔開來,造成兩者之間的疏離與對立,無異是拿著都市居民的利益當藉口在迫害都市原住民。
正如〈空間分離主義與法律根源〉文中提到,建築忘卻其自身的目標之後,就能和協地與鄰居相處,而更能滿足其自身的目標(王槐三,1991:122)。然而建商唯利是圖,技術官僚整天把「依法行政」(誰的法?為誰服務?)掛在嘴邊當護身符,為了都會水岸景觀的偉大建設,剝奪人民生存權益在所不惜。 此外,政府單位的技術官僚在處理河岸部落議題時,總以科技理性(如行水區不能住人、就地居住於法無據)凌駕一切言論,將部落居民的看法貶抑為無知、非理性的情緒發洩,而大眾媒體又過度依賴政府機關的消息網絡,媒介也成為塑造偏見與社會對立的幫兇。
空間的分離同時也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如果都會水岸生活是一種更貼近自然的生活方式,為什麼珍惜土地、在河邊居住耕作的都市原住民部落不在這種生活型態的想像之中?誰又有權為了自己居住或遊憩的目的驅趕另一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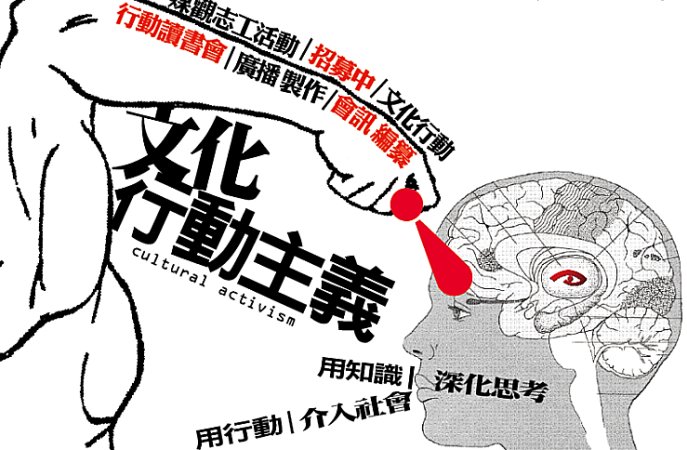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